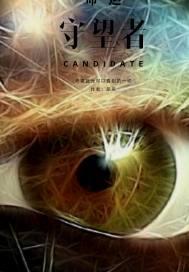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浪儿翻 > 130140(第23页)
130140(第23页)
“那倒没有,”万琛借着执筷的动作,不着痕迹地打量他,“寻到点苗头,东西已经不在北境了。”
“料到了,”阿勒漫不经心,“怎么,在坎西港还是在王都?”
万琛嘴巴紧得很,跳过这句话,说:“十七封信,要集齐不容易,要在战火纷飞里保全也不容易,若是寻到了确切下落,我第一时间为你夺来。”
阿勒有意试探:“若能在半月之内到手,我还能饶你两成利。”
两成!万琛坐直了,他定定地看着对方,倏忽摇了摇头,无奈笑道:“只恨没有确凿把握。”
事已谈定,万琛叫了乐姬来唱曲儿,两人拣着时局又谈了几句。
美人在怀,清乐绕耳,万琛半眯着眼打起拍子,眼风没忘往对座飘,见阿勒懒散地往后靠坐,架着手臂,指头垂下,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。
万琛就不懂了。都是男人,哥舒策这厮,他就跟清心寡欲四个字沾不上边!
生得这样一副欢场老手的模样儿,偏偏每回到他这儿来都跟茹素高僧似的,太定了,也太难撬了。乱伦就这般刺激,刺激到别的美人皆入不了眼了?
他今日心里畅快,便借着酒劲儿开起玩笑:“哥舒公子也二十有余了吧。”
“嗯。”
“家里可有定了亲吗?”
阿勒看过去,半笑不笑:“万大人要牵一回红线?”
“嗨,”万琛就着家伎的手饮了满杯,笑道,“我们万家确有两名待嫁之龄的女儿,只是都娇纵惯了,怕给哥舒公子添堵。”
“万家家风清正,乌溟海这虎狼窝,你也放心姑娘往里跳?”阿勒像是玩笑,晃了晃指头,“谈生意好说,谈姻缘就不必了,我指间自有月老牵了线。”
万琛跟着玩笑两句:“本想占你点儿辈分上的便宜,没想到当真成了家。”
正在这时,重帘晃了晃,龙可羡“散心”回来,看起来还是恹恹的,默不作声往阿勒身旁一坐,就开始揪袖口的毛边玩儿。
龙可羡生了副乖模样,只要不拔刀,看着就怪招人疼,因此万琛看过去,只当小女郎耍得乏了,犯困,他本还想谈谈骊王之事,见哥舒策心不在焉,也就作罢了。
***
马车如何来,就原路回返。
万琛打着哥舒策的幌子,把坎西港里能说得上话的管事聚在西九楼,在他走后,万琛把乐姬一散,琴鼓一撤,拉起帘子,关得严严实实就开始密谈了。
龙可羡手指头卷着马车帘,看九座高楼矗立在红灯流影间,宛如地底延伸出来的异爪,沉默无声地托举着夜色。
“他还要跟你谈事情,”龙可羡干巴巴说,“怎么这样早就散了。”
“要紧的事都谈完了,留下来作什么?等他把家中娇纵的姑娘说给我作小妾吗?”
阿勒把十指交叠着,松松放在腿上,看着龙可羡侧脸,小炮仗上车就没拿正眼看过她。
这话出,龙可羡立刻扭过头:“当真?”
阿勒没答这话,只看着她。
龙可羡把帘子一撂:“好不要脸,别人锅里的也要惦记,只管让他来好了,三山军军营为他大敞。”
阿勒笑,罩着她脸颊揉了个畅快:“酸不酸。”
“一点也不酸,”龙可羡把脖子一横,“谁惦记我的东西,我就要他好看!你,”她目光刀子似的,瞪着阿勒,“你也不好。”
阿勒笑得停不下来,捞着她的膝:“天老爷,即便我心有七窍,淌的都是坏水儿,那也坏不到你头上来。”
“你胡说,我一点也不要信了,”龙可羡不肯坐上去,“你们方才合起伙来算计我,就当着我的面。”
阿勒弹一记她脑门:“算计你什么?你既把我想得那般坏,干脆讲讲清楚,若是有一星半点的冤枉,我就扒你层皮。”
“骊王的船明日就要首发,首发就意味着首归,虽然没有白纸黑字写明,这仍然是我与他默认的协约,你……你偏要听万家撺掇,让士族去拔这个头筹,”龙可羡舌头差点儿打架,“那此前为何还要大费周章捧骊王起势?”
“万琛精于算计,既要在我这讨得方便,又要在士族跟前竖起威信,此番他亟待升调王都,只想把最后的航道办得漂亮,好为进内阁添上把火。送他阵东风又能如何,保不齐飞高了,摔得更惨。”
龙可羡眉毛拧成一团儿了。
阿勒伸手给抚平,直白地说:“你看我像惯爱做善事的吗?”
“不像,”龙可羡脱口而出,“你,坏的。”
惯的她!阿勒使了劲儿,掐住了那团轮廓:“这就得了,事情未成之前,我不爱夸下海口,你且等着看吧。”
龙可羡被掐住了要害,后腰往下都是火辣辣的,她坐不住,撑住了阿勒肩膀,说:“我不疑你,但我身后是二十万三山军,是北境二十六州,你不可骗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