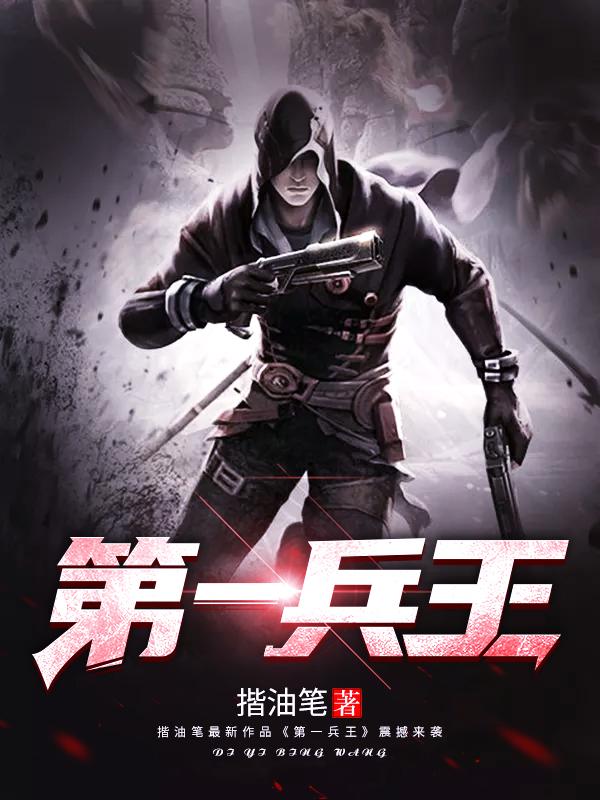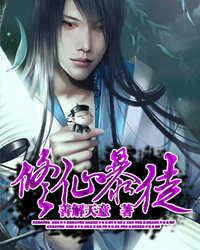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女帝座下第一走狗 > 第559章 甘草台上话天下(第4页)
第559章 甘草台上话天下(第4页)
“我刚得了太仓最新的书信。赵都督得知董公子行将远行,故而赠诗一首,以此送行。”
他本想直接去甘草台汇报,但看到董书生,便决定耽搁一些时间。
否则,等他汇报完毕,只怕整个乐游原都要轰动,这送行诗会也开不下去。
那日在酒楼中,他得知董书生投笔从戎,便有心送别,如今恰逢其会,索性先做了这件事。
“什么?赵都督赠诗?”
话一出,周围人一阵愕然,率先惊奇的倒不是赠诗本身。
赵都安与董书生相识,且为友人……这在京城官场中不是秘密。
当初修文馆初立,恰逢神龙寺召开盂兰盆法会,赵都安前往参加,与人起了冲突。
彼时董公子曾出面解围,此事许多人都知晓。
再加上赵都安在修文馆,也有一层“编外学士”的身份,与董太师相交莫逆。
因此赠诗,合乎情理。
众人惊奇的,乃是白脸缉司言语中透露出的另外一个信息:
太仓府传回消息了!
还是尚未公开的最新消息!
并且,结合白脸缉司最近大半个月消失,不曾露面……真相呼之欲出:
白脸缉司这大半个月,只怕真的离开了京城,去了临封西线一次,或者起码与临封那边的影卫接头了。
否则,他如何能拿到赵都督的赠诗?并亲自代替赵都督赶赴金秋雅集?
“赵兄……他赠诗送我?”董公子愣住了。
性格质朴,在诸多贵胄中罕见守拙的董书生心中一阵感动,竟有些热泪盈眶。
以赵都安今时今日之尊贵地位,却仍旧记得他这个友人,哪怕镇守数千里外,仍旧名人千里送诗,此等情谊,如何不令他感动?
“敢问,诗文何在?”董公子拱手询问。
赵都安笑道:
“诗文在军情密报中,却不方便给董公子看,不过,我可代都督誊写。”
说罢,他迈步走到一方桌案前,捡起一根毛笔,蘸了浓墨,便要在白纸上落字。
一时间,一众文人都蜂拥而至,抻长脖子观瞧。
韩粥也好奇道:
“上次见赵少保诗文,还是那一首《夜记章台》,彼时便觉诗文中有风流气象,今日又有眼福。”
作为一个不合格的文抄公,赵都安公开抄的诗极为有限,只有上次章台宴会上。
“天子红颜我少年”一诗广为人知,如今被坊间奉为顶级情诗……
不过,也有许多读书人嗤之以鼻,认为赵都安以诗文献媚女帝,有辱斯文,且那夜记章台虽字句惊艳,但若说有多深的功底,令人信服……却也没有。
在读书人的印象中,赵都安一个武人,哪怕有些才学,但诗文并不擅长。
只不过,今日不同往日,以赵都安的身份地位,哪怕写的再差,也没人敢公开贬低。
甚至会有许多人谄媚吹捧。
这时候,就已经有一些人绞尽脑汁,思索等下该从哪种角度吹捧赵都督写的垃圾诗文了。
韩粥都在思索,若诗文平平,自己该怎么点评才不失体面。
然而赶时间的赵都安已经落笔,故意改了改习惯的字迹。
一边写,旁边韩粥已轻声念了出来:
“《别董大》……”
“千里黄云白日曛……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