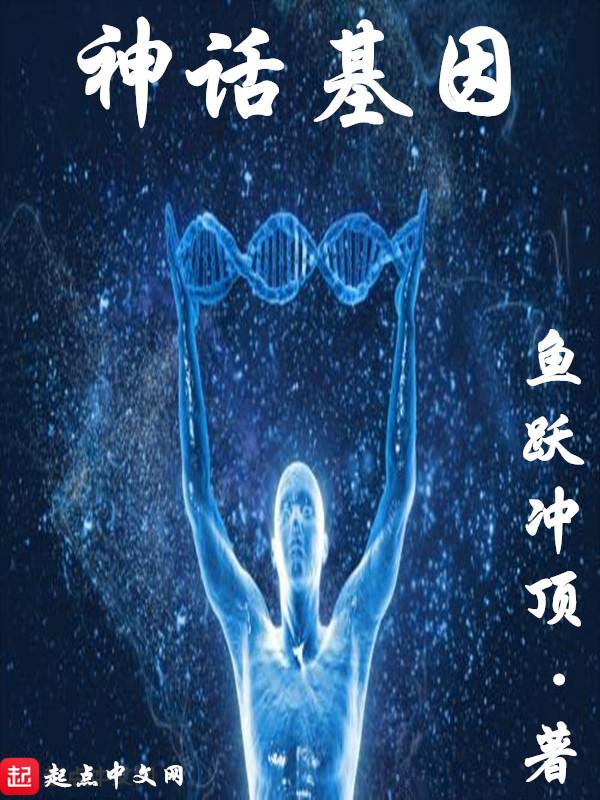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魔尊你就这点出息? > 90100(第31页)
90100(第31页)
纵然是在难行的山道上,他还是能遥遥领先,甩开身后的人。
不过之前他一直藏拙,刻意混入人群中,跟在护法身边。
两个小崽子牙尖嘴利,不注意被咬一口,嘶,那可疼得很。
一路追赶,被他们两也杀了许多高手。
但是眼下,明眼人都能看清,他们只是强弩之末,撑不了太久。
他看上两人的皮了。雪白的皮,殷红的肉,正适合慢慢剥下来,做个漂亮的“纸人”呀。
道路逐渐变得平坦,只是路上杂草疯长,绿藤垂地。
这似乎不是陡峭偏僻的山道,而是条废弃的官道。
纸扎匠脑中无端闪过这念头。
“嘶——”
他听见一声螺马的嘶鸣,不由回头望去。
月光明澈,洒在地上,天地清明如水。水底摇曳着许多影子。
有牵马的游子,有螺马拖车的商队,还有倒骑毛驴的酒客。
他们谈笑风声,在道上行走。
杂草疯长的道路,不知何时,也变成一条宽阔的官道。
纸扎匠遍地发凉,回头望去。
两座雪峰如同尖刀插向云空,银白月光明晃晃,两山之间,一座繁华城池巍然而立。
城门刻二字。
“枌城。”
……
明明是夜晚,明月当空,城中却许多人走动。沿街站满摆摊的商贩,楼上探出许多个脑袋,好奇地望着来人。
月光照在一张张惨白的脸上。
扎纸匠浑身冰凉,后脊蹿起凉气——他意识到不对时,已经不能回头,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。
“哟,客官,来口酒吗?”
扎纸匠闻声望去。
是个笑眯眯的掌柜倚靠柜台,抄着手,说道:“我们家的枌酒,试问沧州谁不知道,来往的客商都要尝上一口。尝一口,疲惫祛,第二口,百病消,客官,您来试试吗?”
扎纸匠本想拒绝。
但老板却从柜台走了出来,殷勤迎客,“来嘛来嘛,不喝口咱们家的酒馆,怎说能到过枌城?”
“沙沙——”
夜风吹过,满城绿叶飘摇。月光如银色的轻纱,在满城深绿浅绿的酒花上流泻。
“是枌花。咱就靠这酿酒呢。”老板把毛巾往肩膀一搭,笑面迎客,“客官请进。一壶枌酒!”
“好咧!”
伙计高声吆喝,“一壶枌酒,马上就上,客官且选个位置坐坐!”
扎纸匠扫了眼四周。
这家叫章氏酒坊的酒楼生意确实不错,大厅八张桌子,其中有四张已经坐了人。
他找个角落靠近门的位置坐着,打量酒楼的动静。
章氏酒坊看上去平平无奇,似乎只是间生意好的小酒楼。坐在其中喝酒的几桌,一桌是白发老人,长指甲剥着花生衣,慢条斯理地吃下酒花生,偶尔才酌一口小酒。
一桌是落拓的书生,醉得不清,趴在桌上,嘴里呢喃着什么“山月不知心底事,水风空落眼前花”。
还有一桌。
是一家三口,精明能干的妇人,留着山羊胡的商贾,还有个坐在凳子上晃动双腿的小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