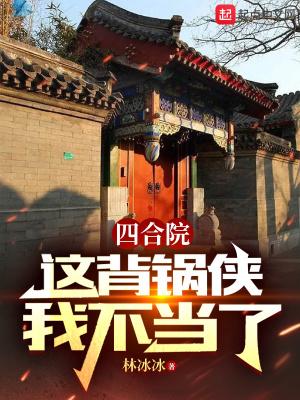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被儿媳摸到硬的公爹 > 第41章(第3页)
第41章(第3页)
“你要带什么,要用什么,自己也不看看,只顾着喝酒,到时候要用了没带上,看你找谁哭!”
青黛看不过去颜凝这死人不管的懒散样子,简直想狠狠揪她耳朵骂一顿,可又知道她心里难过,说了两句也不逼她,一个人全权替她拿了主张,衣裳用具都打点得妥妥当当。
谢绥十分舍不得颜凝,握着她的手要她多写信回来报平安。
江氏虽然因为之前的事怨过颜凝,但听说她要走,心里也不好受,让她放心家里,会看好谢慎不许他再和谢老爷对着干了。
余姨娘过来说了几句客气话,谢衡也来看望安慰她,大家都如此沉痛,让她有一种“自己这是一去不复返了吗”的错觉。
谢景修则又去了宫里面圣,没人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什么,只看见谢阁老被永嘉帝赶出大殿,在寒冬的石阶上整整跪了两个时辰,到最后淅淅沥沥下起了冬雨,才开恩允他起身,也不见他,只让太监传话让他走。
浑身湿透面色惨白如纸的谢阁老先去内阁值房换了一身干爽的衣裳,阴沉着脸也不理人,由侍从打着伞怒气冲冲走去午门坐马车回府。
谢慎在翰林院听说了父亲开罪皇帝被罚跪淋雨的事,赶忙过来看望谢阁老,谢景修却对他视而不见。
他跟了一路看到父亲撩起衣袍要上马车,立刻喊了一声“父亲”伸手去扶他。
谢景修心情恶劣,转过头来阴着脸冷冷瞥了一眼长子,手臂把他伸过来的双手漠然往外一推,自顾自上了车离开了。
到了家里谢老爷立即吩咐让人备热水沐浴,大寒天里跪了那么久还淋了雨,这种时候可不能病倒。
在他眉头堆成山,双目紧闭泡在浴桶里的时候颜凝进来了。
“爹爹,怎么淋雨了?”
谢景修睁开眼睛看了看她。
娇娇怯怯,凄凄愁愁,娉娉婉婉,媚姝灼花一朵,琼娥仙草一株,应作掌上舞,岂可送边营?
他暗暗叹了口气,沉声命令:“和你没关系,你把衣服脱了进来。”
颜凝柔顺地除了衣衫跨进桶里,被谢景修从身后搂在怀中,她原以为他又要做些什么,拿她撒气,或者泻火,可是他只是抱着她,反复盘弄她十根纤白的手指。
他轻轻揉过她双手上每一个指关节,又翻过来看她的掌纹,挨个捏过一粒粒肉鼓鼓的指腹,与她掌根抵掌根,合上两人的手,比她长出整整一个指节,最后与她十指相握。
“送你的印章别弄掉了。”
“嗯,不离身,您看,我洗澡都戴着。”
颜凝举起挂在双乳之间的琥珀转身给他看,被他接过去放在唇边亲了一下再还给她,她则拿起来对着光细细观摩,好奇地问道:“爹爹,这里面红色的小虫子是什么呀?”
“红豆蚁,是个难得的稀罕物,花钱也未必买得到。”
红豆蚁表相思,谢景修当初得了这个小玩意便束之高阁,没想到居然有用上的一日。
他看着颜凝天真娇艳的侧颜,心中闷痛,突然试探地问她:“今晚爹爹如果要把精元弄到阿撵肚子里面,你答应吗?”
“啊,这……爹爹……”
看到公爹问这话时一脸景容,颜凝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,她要走了,可不能在这当口怀上孩子。
“罢了,什么都留不住你。你是凝,我只是雁,终归留不住你,也追不上你,你去罢。”
他又闭上眼靠在后面,似乎不想再说话了,眉间皱褶又深了几分。
“爹爹,我会回来的,您等我。我一天都不想离开爹爹,就算人不得不走,可心早就被您留下了啊。阿撵这一生已经离不了爹爹了,您难道不知道吗?”
颜凝转过身来趴在他身上蹭着他的脖颈,痛到肝肠寸断,却说不出什么聪明的话来安慰他。
谢景修环住颜凝娇小的身躯,睁眼痛苦凝视她,“我担心……我怕万一战败……”
他的声音几乎发颤,她不忍让他说下去,毅然决然打断他:“不会的!就算战败我也能带着表舅逃出来,您记不记得我夜闯御书房偷玉璧?
禁军连我的影子都看不到。爹爹的字写得有多好,我的轻功就有多厉害。”
疲惫的次辅大人终于露出一弯浅笑,“那真是挺厉害了,不过你这个字写得和蚂蟥一样的人哪里分得出别人字好坏?”
“爹爹再这样说我我要生气了,谁写字像蚂蟥了。”
“不但写字像蚂蟥,在床上扭来扭去的时候也和蚂蟥差不多。”
“生气了,今晚要榨干爹爹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