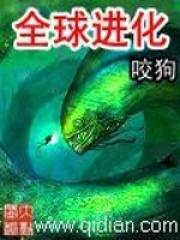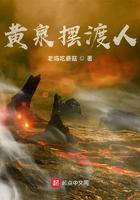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清穿甜崽胤礽直播间 > 220240(第40页)
220240(第40页)
地上的荒草干枯横楞着,发出细微的摩挲声,摇摇晃晃,厚重的枯草下面,隐约透露出一点点翠绿,那是躲藏了一整个冬天的生机。
更远的农田里,有农人顶着寒风正在田里劳作,去年下的雪不小,希望今年也是个丰年。
“你知道的怪多呢~”康熙说道。
李礽翻身,手肘架在车窗沿上,他感觉到了一股子的阴阳怪气呢,“是啊,都是汗阿玛教得好。”
康熙把书丢到一边,“哦?”
“汗阿玛,还是丰泽园的农作物种得好呢。”李礽又瞅了车窗外的农田一眼。
他上次去看丰泽园的田,那绿油油的麦子,就像是蓬松的长绒毯子。
而这次看到的农田,疏密不均,很像是脱毛的癞皮狗。
康熙凑近,将车窗口推得更大,看了一眼,“确实差了些。”
“为什么呢?”李礽问道,他对种田大概是七窍通了六窍,一窍不通。
“原因很多,比如说施肥不均,或者播种不均,又或者地没有耙好。”康熙说道。
李礽盯着外面看了一会,“我觉得咱们可以把这些农业技巧面向全国推广,提高粮食产量。”
“这些技巧都十分零散。”康熙顿了一下,又问道:“你既然提到了,可有什么主意?”
李礽问道:“您有什么办法吗?”
“授官制,个中突出之人授官,你觉得如何?”康熙问道。
李礽……大清的官职不是大风刮来的,但是是被大风刮走的。
虽然保成没有说话,但是他那一言难尽的表情和连绵不绝的沉默表明了一切。
康熙也觉得自己这个建议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妥,但是他死撅着不肯承认,还有点恼羞成怒,道:“那你说来听听。”
“先将一些春耕的技巧整理出来,写得翔实一些,可别弄些佶屈聱牙的华丽辞藻,平实易理解,以公文的方式传递到各地,让人提前了解。”李礽说道。
“谁来整理呢?”康熙问道。
“武英殿那么多人,总是有些闲人,再不济从进士里面再点几个人呗。”李礽说道,只要康熙开口,这天下,大把的人都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地冲上去。
“你倒是想得好,武英殿的人岂是给你做这个事情的吗?”康熙失笑。
武英殿是在永乐年间建成,是大型礼节活动举办的地方,在李自成的那把大火里面侥幸逃过一劫。
后面清军入关之后,延续武英殿在前朝的作用,作为举行典礼的地方。
前两年,他将武英殿辟出来,设置了武英殿书局。
左右两边连廊处的偏房腾出来作为修书处,里面的官员拢共三十多人,由他亲派,也有部分是翰林院派过来的人,总理之人是亲王大臣。
这样的地方,让他们去处理这种东西,那可是杀鸡焉用牛刀了。
“汗阿玛。”李礽叫了一声。
这突然的正色让康熙的心都跟着使劲跳了一下,咽了一下口水,才道:“怎么了?”
李礽揣着小手炉正经地说道:“您知道为何您反复强调农桑之重要,但效果仍不明显吗?”
这话题跳跃太大了吧,如何把武英殿修书和丰泽园种地扯到一起的?
康熙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,扬了扬下巴,示意他继续说。
“因为您也不是真心看重的。”李礽说道,“您自己在心中就给这天下的人划分了三五九等。”
这话极为大逆不道。
康熙瞪着保成,凶神恶煞,半晌都没有说话,他哪里不是真心了?
“都是修书,难道诗词歌赋、史学典籍就比农桑之书高贵吗?再说,武英殿书局本就是修书之处,我们授予他们官职,就是让他们做这个事儿的,岂还有挑挑拣拣的余地?”李礽说道,“不愿意就换个人呗。”
康熙听着他的解释,反问道:“那跟朕有什么关系?”
“汗阿玛,您张口就说武英殿的人不愿意做这件事儿,岂不是说明在您的心里也认为农低士一头?”李礽摊手耸肩,非要自己说这么明显,真是一点余地不留啊。
仔细想想,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,康熙轻咳一声,食指指节顶了一下鼻子,“朕只是顺口一说而已。”
人总是在无意间流露之中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,“士农工商”喊了这么多年,不是流于表面,而是根深蒂固的想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