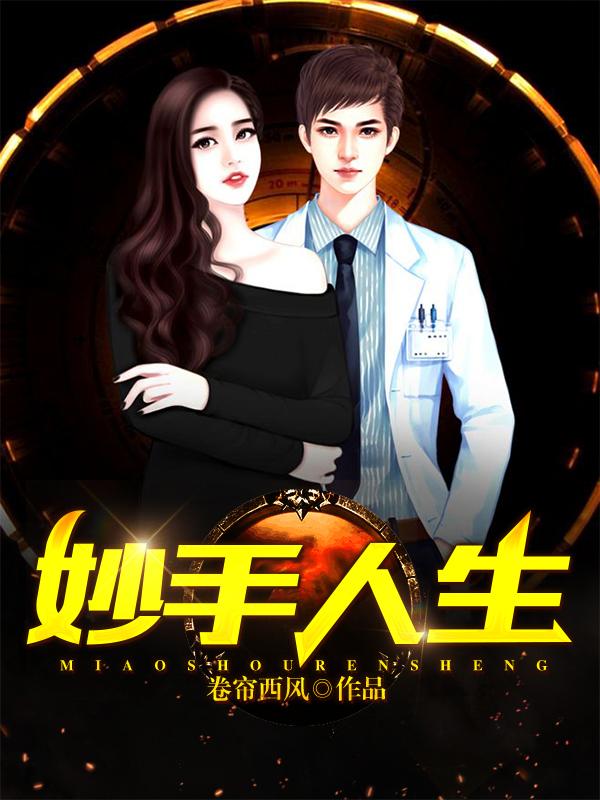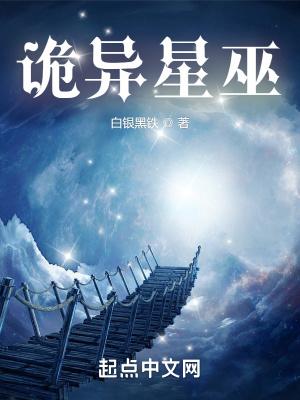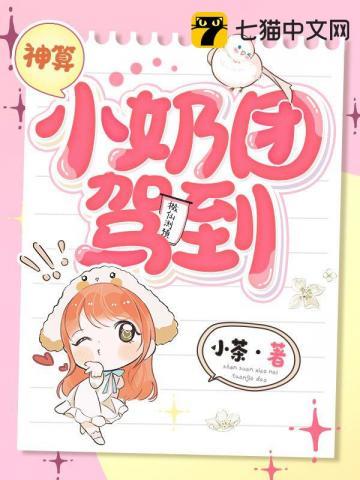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我的老婆是黛玉[红楼] > 120140(第13页)
120140(第13页)
“好,你去吧。”连夫人还是忍不住交代道,“你与大郎是骨肉至亲,父子兄弟之间,没有什么是说不开的。”
“我知道了娘,您也忙了一天,快去歇着吧。”
目送连夫人关上了卧室的门,他才从后门去了徐景行夫妻的小院子。
自从他们回来之后,徐樗和徐桂姐妹跟着他们搬到这院子里住了。据黛玉所说,甄夫人和他们兄妹相处得还算好。
这得归功于两个孩子都比较懂事,黛玉和他们细细分说过甄夫人当初怀着他们走流放路的不易,还有产后抑郁症有多严重。
又说了甄夫人得了产后抑郁,周围的人却都不明白这种病症的厉害,对她的变化不理解,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
虽然对孩子用恩情教育不好,但甄夫人毕竟情况特殊。无论是公婆还是丈夫都不能理解她,甚至他的娘家人也会觉得她矫情。
如果她的孩子们再不能体谅她的苦楚,只怕她会觉得天塌地陷,很容易把林黛玉这个唯一能理解她的人当成救命稻草。
若真发展成那种情况,日后甄夫人再遇到什么坎儿,只要林黛玉的反应有一点不符合她的预期,她都可能彻底崩溃,做出过激的行为。
两个孩子和母亲相处时,虽然心有顾忌,不敢肆意撒娇耍赖,但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因为他们并不缺少母爱,从不满周岁一直到虚五岁,他们身边一直有合格的母亲角色。
自小不缺爱的孩子,更容易释放爱,也更愿意付出爱。
因为他们有底气,不怕受伤,自然敢肆无忌惮地释放付出。
恰巧甄夫人也是第一次做母亲,不知道正常的母子之间究竟如何相处。
再加上如今的社会氛围里,孩子乖巧听话就是孝顺的表现。她对两个孩子很满意,也对把她的孩子教的这么好的林黛玉很感激。
总而言之,在这件事情上,算是皆大欢喜。
小院里的灯也没有熄,徐景行来开门时,衣衫还十分整齐。
看见徐茂行,他笑呵呵地说:“怎么,你也读书读到这个时候?还是睡不着,来找我说话?”
他的态度和当年没有任何区别,但徐茂行自幼和他关系极好,对他非常了解,自然能看得出来,他身上比当年多了一种紧绷的情绪。
那是一种迫切,对于改变现状的迫切。
从通衢回来之后,徐茂行就从母亲连夫人那里了解到,就算是在平安州时,徐景行也没有放弃读书。
虽说因着安王的关照,他们一家生活平稳吃喝不愁,但也仅此而已了。若想要得更多,就得靠他们自己。
徐景行就每三天徒步去一次十里外的镇上,只因那里有方圆百里唯一的书铺。
他在那书铺里接了一个抄书的活儿,用挣来的钱买纸笔。
抄书嘛,肯定有不小心抄坏的时候。
因而每次领新活儿时,对方给的纸都会多出七八张,防备不慎抄坏了可以替换。若还有剩的,那就是抄书人自己的福利了。
为了省下这几张纸,徐景行每次都专心致志,尽量一遍就写成,不多字、不少字、不错字、不脏污。
砚台和墨都是他自己做的。
前者还好说,只要找到了质地合适的石头,自己琢磨一个也花不了多少时间。
最难解决的是墨。
好在平安州苦寒之地,多松柏之属。他自己挖掘腐烂的松根,又找了一个人家不要的破缸,小心翼翼地试着烧松烟。
每天烟熏火燎,不但脸上脏兮兮的,擤一下鼻涕,出来的都是两条黑。
因做冷凝的只有一口破缸,收集松烟的过程极为缓慢。好不容易制成了两锭松烟墨,他自己根本没舍得用,拿到书铺子里,去换了便宜的臭墨,就因为那个量大。
凑出了笔墨纸砚后,他就请父亲徐甘,给他默写科举要用的书和注解。
种种艰辛不必多言,徐茂行只听了一次就唏嘘不已。
原本他听了郭先生的分析,觉得一母同胞的两兄弟,骤然间遭遇天差地别。两兄弟中一直是强者的兄长忽然掉到了下风,心中肯定会不平。
他也因此心中生出了些许防备,不是为了别的,只是不想不明不白吃亏而已。
可听了母亲的讲述,知道大哥纵然落入泥沼也不肯放弃努力,他就知道郭先生虽是一片好意,分析得也符合人性,却并不一定能套用到所有人身上。
至少他大哥徐景行,是绝对套不进这个框架里去的。
只因傲骨不折的人,有心超越别人也只会努力提升自己,不会想着用卑鄙的手段阻拦别人的上进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