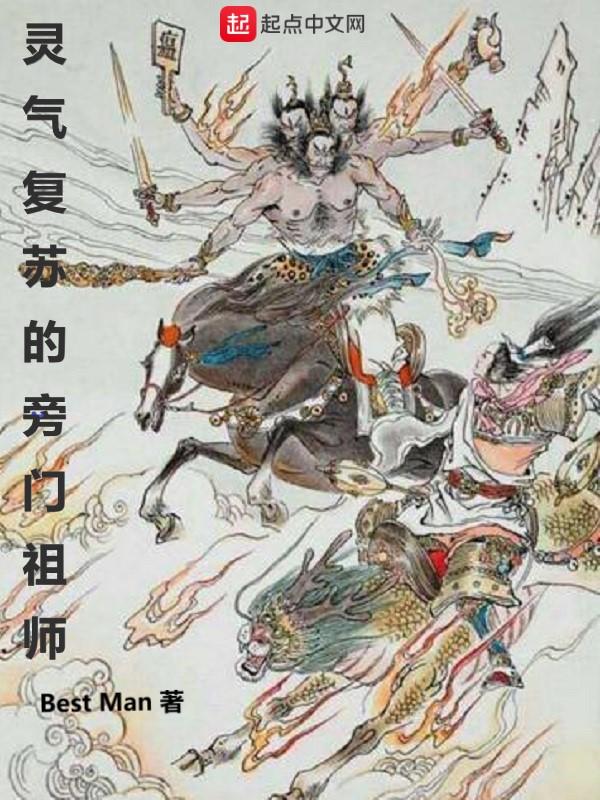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人下人巧善 > 130140(第20页)
130140(第20页)
“不是只有我们,她,她们,本来都可以的,只是一早就被扼杀了。褚颀,我知道这桩婚事是你父亲为了报恩定下的,但无论如何,你都不能伤害她,因为你只有父母之命不可违抗,而她身上压着重重大山,更没得选!”
他知道,正因为清楚这点,才会这么痛苦。
她接连向前走了三步,拿木尺那头顶着他,盯着他的眼睛说:“不要想着给名分,有没有她,我都不要,谁也别想再困住我。我只惦记一件事,我在她跟前说了,她不生气。你要是愿意,拿下清源县,就来找我。”
这一次不同,他脸上没有臊,只有叫人看不透的深沉。
两人对视良久,他摇头,眼含深意说:“我不能伤你。”
“迂腐!”
嘴上这样骂着,心里又喜又气。
喜的是这样的男人太难得,不能娶她就宁愿忍着。怕提起赵至忠的龌龊让她难堪,就宁愿被误会,挨骂也不肯答。
要维护这个,要尊重那个,才会总是一副“我有话,但我不能说”的磨人相。
本来她是为了赌气才起的这心思,如今她不恨徐风芝了,也不恨他了,但这事念得多,就成了执念,没达成,实在心痒痒。
偏偏碰上个死脑筋,这露水情缘怎么也成不了!
“不愿意,那你还来?不怕被我霸王硬上弓?”
她不怕事,他怕,明明耳朵好使,还特意退到外边查看,回来见她捂着脸在偷笑,又心满意足了。
“来了就别闲着,搭把手,按住那头。”
他扯出帕子擦了擦手,再帮忙压住布尾。
她利索地一笔裁到头,他看会了,很机灵地帮忙将新的布头拉过来压好。
“这个花色怎么样?”
“好看。”
“替她裁的,不是你叫她穿那么死板的吧?”
“不是。我没留意过她穿什么。上边每年有赏赐,先紧着她们选,余下的,再分发下去。”
“那就是……褚颀,将来你要是跟那清风宜人有点什么,哼,我天天扎小人,诅咒你们!”
“谁?不会有什么。”
“别装糊涂,记着这四个字!”
他又说一次:“不会有什么!”
她用完就轰人,“赶紧走,我们要‘睡’觉了!”
睡字咬得重,叫人绷不住,可是他不能。
隔壁有王姑娘教妙妙认物的声。
是该走了。
他掀起棉帘子,忍不住回头瞧她。
她也在看他,抿着嘴,瞧不出喜怒,但眼珠子在闪光芒——像是又在琢磨什么耍弄人的主意。
他移不开眼,不觉停了下来,“那是我们安排的人,古本要归库,也是罪证,不能退还。你愿意加价三成,他装糊涂说没这本。你再背律法,叫他知道一经查出,要杖打,要坐监。他反过来威胁要去官府告发,你没有露怯,猜了一堆当铺弄虚作假的坑骗招数,要敲锣打鼓昭告……”
她抢着说:“知道是这么个混子,你还敢招惹?”
“你猜的那些,全中了。聪慧机敏,知礼懂法,胆大心细,自强不息……这很难得。”
她头一回认输,转开脸,避开这深邃的目光。
“我只是不想被他牵连受罪,没那么大公无私。”
祖母决定去死的那一晚,一直在劝她们放下怨结,认命吧,等着他们在那堆有钱的老鳏夫里挑好了,就乖乖地嫁过去。
过日子,嫁谁不是嫁,年纪大的更疼人。
祖母最终觉得是自己做错了,不该教她们读书思考,因为女人永远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,想不透,浑浑噩噩一辈子,反而没那么痛苦。
赵至忠巴结上了姓赵的那一家,上了榜。她跟着水涨船高,官家小姐嫁老财主不划算,押送去京城严训严教,待价而沽。
母亲往日拿到钱就喜笑颜开,接了丈夫的信立刻变脸,以死相逼,让舅舅反叛,把她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买卖掐断,帮她的人全被严惩,婉如和红衣险些被打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