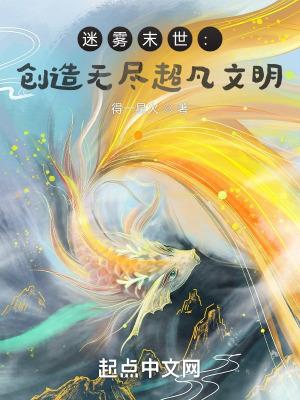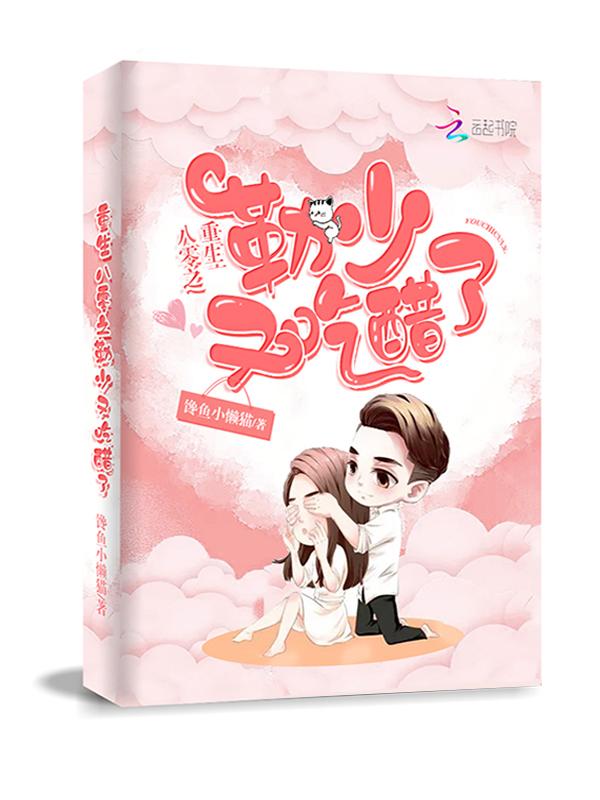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人下人巧善 > 130140(第22页)
130140(第22页)
赵西辞也笑,柔声交代:“你们青梅竹马,情分深。这半路来的情不牢靠,易生变,我没指望它。这事还得再筹划筹划,我要好好想想,怎样才能将他的好维系得长久。还有风芝姑娘,她也有用。”
“好,这事只有我们知道,我不告诉一个人。”
赵西辞最爱她的暖心,故意说顽话:“我要是个男人,一定娶你,可太舒心了。”
巧善跟她待久了,经得起玩笑,顺口反击:“快别说了,他一直防着你呢。”
还真是,扶个腰都要吃醋,挨着坐也要盯来盯去。
全心全意爱一个人,就会这样时时刻刻想独占吧?由此可见,她对褚颀,只有感动,触动,没有真的爱上,徐风芝也不爱他。
真可怜!
“西辞,既然人心浮躁于我们有益,那在这里也能用吧?那批羊最晚后日早上能到,留到攻城那天再煮。眼下刮的是北风,正好……难的是没有那么多大炖锅。”
赵西辞一听歪主意就乐了,“有!寺里必定有,不肯借就抬它家的香炉,拆它家的钟,拿来当锅使。”
这是顽话。
得道多助,褚家军一到,主持领着一众和尚迎到了山门外,帮忙安置救出来的老幼病残,将功德箱清空,拿来捐助,把后山种的菜摘来相赠。出钱又出力,有什么给什么。
赵西辞见多了人心险恶,又有话说:“他们打惯了清水仗,智谋都在排兵布阵上,一直顺风顺水,未必肯用。这事等褚颀过来了再说,愿不愿意的,让他去定夺。巧善,皇城是个邪门的地方,离那越近,人就越怪,你早做准备。”
“你是说,我们身边这些人,也要起心思了?”
“嗯。输了有输的心思,赢了有赢的心思。有权势的地方就少不了争斗,原先跟着的,半道来投奔的,战时收服的,还有我们这些没有正经投军的散人……”
“好,我知道了。我原以为不去做官,就不用懂蝇营狗苟怎么写。怪我忘了为人处世的门道也多,还得好好学。”
赵西辞怕吓坏了她,特地问:“裁那些布,本钱是多少?拿出去卖,又是多少?我心算不如你,你替我算算,明儿我找她讨钱去!”
巧善闷笑,“你呀,又淘气了!缎只用在了花间裙的细缝里,两色加起来才一尺出头。八样布,算上耗掉的碎布头,也才五两七钱,按往年的价卖,该是八九两,今年的行情不对,最多能到七两半。鞋子有现成的,我絮好了棉塞子,明早缝上了再给你。账都算完了,手头上没活,来得及。”
“不是我惦记那三瓜两枣,徐风芝前半辈子一直被他们当成摆设,指定乐意被人索取。看见!巧善,人最怕不能被看见,伤心,欢喜,得意,失落,努力……”
巧善很自然地接道:“是啊,有人见证才好。不论男女,有个人在就是好的。”
在王家时,她就是那个不被看见的人。大哥是好人,但他也艰难,多数时候自顾不暇。有了小英,她才像个人一样活着:关心,被关心。小英走后,她又有了他。他离开几年,她还有梅珍,有青杏。他又回来了,他们再也不分开,还多了别的兄弟。接着是西辞、婉如她们,将来还会有更多。
赵西辞摸摸鼻子,接道:“没有人,猫猫狗狗也可以,带眼睛就行了!”
巧善又被逗笑,应道:“会越来越好的!西辞,我们这么努力,有资格问老天爷要一份回报!”
“嗯。睡吧,过几日,又要在车上颠簸了。”
行军打仗要力气,吃得饱力气才足,她们这没有精米吃,但不仅有粮,还有菜,绝对管饱。
十天半个月吃一次肉,天冷了,一碗热乎乎的肉汤下肚,能把五脏六腑哄得服服帖帖。
每回到前边去报账,总有人注目或是抱拳行礼,还有那胆大的,特意凑上来,叫一声“王大人”,“赵大人”。
这对她们来说,是莫大的鼓舞,因此钱一到手,就想着再去找点荤腥回来给他们打牙祭。
天冷了,得防着伤寒、风湿和冻疮,还要采买药材。后来的兵没有棉衣棉裤,也得供上——再往北,就要对上冰天雪地了。
褚颀和他父亲都镇守过西南,那里的人代代感念褚家军的恩德。官员接了出兵的旨意,但不敢轻举妄动,一是粮草供不上,二怕还没出门,本地也造反了。包抄指定不成,极有可能没走出二里地,就被百姓抄了底,只能先拖延。
西南无战事,可以去探探。
她们在天黑后悄悄地离营,接着搜寻过冬的物品。
被拐带出来的徐风芝一路忐忑,巧善和赵西辞夹着她哄,每到一处,都把她拉下车来看看,让她认认地方,看看百姓过的什么日子,谈买卖也要带上她。
这些事,对她来说都是新奇的,尤其是看到赵西辞骑羊摔下来,险些吓晕过去。
赵西辞大笑着多滚了半圈,赖在干草地上撒娇,好姐姐好妹妹地喊,叫她们过来帮她除草屑草针。
她们忙着帮她清理,她惦记上了吃的:“这羊一身的力气,腱子肉指定香,今晚就尝尝。”
徐风芝捻着手里的草针,忘了阿弥陀佛,只记得笑。
小留带一队人守着熏猪羊,她们接着往南走,买到接骨散再回来会合。
带的人手不少,轮番赶马,日夜兼程追上去。
拉回来的东西还没交完,一落地就得了个坏消息。
有人趁她们不在,要带走廖宝镜,说什么“大河有水小河满,大河无水小河干”,叫她顾全大局,去招降曾经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曾总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