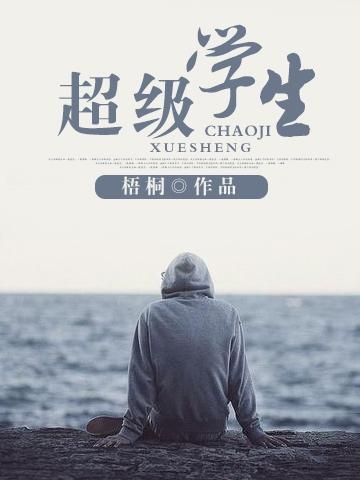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我的聊天群里全是女频窝囊废 > 第266章 再考一次(第4页)
第266章 再考一次(第4页)
太傅和李文渊强压下怒火,也同意了这个提议。
很快,两人便商议着,临时拟定了一份难度适中的新考卷。
姜妙颜拿到考卷,看也不看题目,再次提笔就写,依旧是那副胸有成竹、随心所欲的模样。
片刻之后,她将答卷递上。
太傅和李文渊接过卷子,当场批改起来。
然而,越看,两人的脸色就越是难看,眉头也越皱越紧。太傅是怒气未消又添堵,李文渊则是连连摇头,眼中满是失望。
最后,两人对视一眼,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无奈和……果然如此的意料之中。对于这位大公主能写出什么东西,他们早有心理准备,只是亲眼看到还是忍不住扼腕。
太傅放下朱笔,几乎是带着一种宣布罪状般的沉痛和厌烦,看向姜妙颜,声音干涩地宣布:“大公主此卷经核查,谬误百出,无一处可取,评为……劣等!”
“什么?!”姜妙颜如遭雷击,尖叫道,“全错?!不可能!绝对不可能!你们肯定是故意判错!本宫再不济,也不至于一题都答不对!你们给我解释清楚!哪里错了?!”
“好,既然大公主执迷不悟,老臣便与你分说一二,也好让你心服口服!”太傅强压着怒火,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声音,拿起卷子,指着第一题,“此题问:‘《尚书》有云:‘满招损,谦受益。’请结合本朝高祖创业及太宗守成之史实,论述此言对君王治国理政之警示意义。’
此题考较经义理解与史论结合。大公主却答:‘高祖、太宗那是天命所归,自有龙气护体,哪来的损益之说?这就是胡说八道!’
大公主!圣人经典,乃千古不易之理!高祖披荆斩棘,太宗励精图治,皆有赖于戒骄戒躁,从谏如流!你竟将此治国警言视作无物,反而鼓吹骄纵自满,此等见识,你都学了些什么?!”
他又指向第二题:“此题问:‘本朝于北方边境设九边重镇,互为犄角,以御外敌。然近年来,边患频仍,粮饷转运不畅。请就‘加强边防,稳定粮运’提出可行之策二三。’此乃策论题,考较对军政实务之认知。
大公主答曰:‘边关蛮夷,不过癣疥之疾!派大将领兵,直接踏平便是!至于粮饷?国库有的是钱,要多少给多少!转运不畅,那是下面的人无能,砍了换人!’
大公主!边防乃国之大事,岂是‘踏平’二字就能轻言?粮饷转运涉及调度、民力、耗损诸多环节,国库亦非取之不尽!你对此等军国要务毫无认知,只知喊打喊杀,推诿塞责,甚至轻言斩杀官员!此等狂悖之言,若为施政之策,必将祸国殃民!”
太傅只讲了两题,便感觉筋疲力尽,于是李文渊便顶了上来。
他板着脸地拿起卷子,指着一道算学题,说道:“此题问:‘今有河堤一处,需加固。按工部测算,共需土石方三百丈,民夫五百人,预计工期二十日。若欲将工期缩短至十五日,问需额外增派民夫多少人?’此题考较筹算与工程配比之基本。大公主倒是在卷上写了演算过程,只是……”
李文渊深吸一口气,努力平复情绪,才继续念道:“大公主先是将原有民夫数五百,与缩短后的工期十五,不知为何竟做起了加法,写下‘五百加十五得五百一十五’。随后,大约是觉得这个数字不妥,又将其划掉。接着,她又尝试用原有工期二十去乘民夫数五百,然其演算潦草不堪,墨迹斑斑,最后竟得出一个‘一千’的结果!”
李文渊指着那个刺眼的‘一千’,声音陡然拔高,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愤怒和荒谬:“大公主!五百乘以二十,乃是整万之数!您是如何得出‘一千’这个结果的?!便是让三岁蒙童掰着指头数,恐怕也比您这演算要准些吧!”
他强压下想要将卷宗摔在地上的冲动,继续道:“更荒谬的是,您得出此数后,竟直接将其批注为‘所需增派民夫之数’!全然不顾题目所问,亦不理其中比例关系!这、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算错,微臣根本理解不了你的思路!”
太傅和李文渊将姜妙颜卷子上的几处典型错误一一指出,每一处都错得离谱,错得荒谬,充分暴露了她知识的匮乏和思维的混乱。那些答案,有的颠三倒四,有的胡言乱语,就不像是一个接受过教育的正常人能写出来的。
听着一条条被批驳的答案,姜妙颜瞠目结舌,她想要反驳,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反驳,因为她甚至都听不懂面前这俩人在说什么。
“骗人!骗人骗人!全是骗人!我怎么可能会错!”姜妙颜忽然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,她猛地后退几步,怨毒地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——楚路、太傅、李文渊,甚至包括旁边的太监。
“你们都串通好了!都是一伙的!就因为柳佳佳是个蠢货,拿不到头名,你们就合起伙来欺负我!针对我!”她大声尖叫着,眼中充满了刻骨的恨意,“老东西!你给我等着!这件事没完!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!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!一定!”
说完,她不再看众人,转身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御书房。
太傅和李文渊面面相觑,又不由看向楚路。
楚路则是神情轻松。
他从一开始就没指望姜妙颜会老实认错,能够将其逼退,就已经达成目的了。
自然心情愉悦。
他对那两人说道:“行了,没你们的事了,下去吧。”
两人如释重负,连忙躬身行礼:“臣等告退!”
说罢,两人便离开了御书房。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