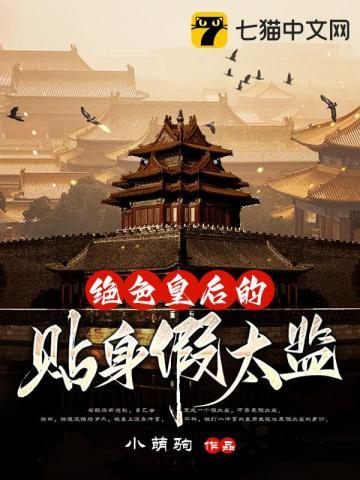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至死靡他 > 2030(第19页)
2030(第19页)
nbsp;nbsp;nbsp;nbsp;啪地!
nbsp;nbsp;nbsp;nbsp;利落有声。
nbsp;nbsp;nbsp;nbsp;“你够了!”
nbsp;nbsp;nbsp;nbsp;女声嘶哑的怒吼贯彻整条廊道,她居然也忘记去在意会不会引来别人。
nbsp;nbsp;nbsp;nbsp;“很好玩吗?”音嗓坠沉,开始条条质问他:“为什么你问什么我都要回,你说什么我都要听,陈既白,你干嘛要那么无理呢?你干什么只捉弄我呢?”
nbsp;nbsp;nbsp;nbsp;陈既白就怔那儿了,垂眼迷蒙,缓缓看到女生潮润的眼,侧脸渐渐生红,做不出反应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完全不能体会梁穗此刻激怒,她是真厌透了这种被耍得团团转的感觉,整个人还处于极度紧张与怔忡当中,刚挣脱桎梏的肩在微颤,双目充裕嗔怒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咽了咽喉,听着不知道哪边传来的开门声,冷冷直视他,说最后一句话:“不是要条件吗?那就现在兑换,我要你,今后都别出现在我面前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他也那么站着,听着,清闲随意的姿态浑然不见,低气压,两只手都揣回兜,一句话也不说,良久后抬手,指节给她蹭了眼角的泪,可能想道歉,字音没吐出来,梁穗就先推开他,转身走了。
nbsp;nbsp;nbsp;nbsp;……
nbsp;nbsp;nbsp;nbsp;……
nbsp;nbsp;nbsp;nbsp;开门出来的乌昭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副脸色的梁穗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她从拐角走出来,身后没跟人,眼睛红,唇色白,低靡地摆着步,空洞地望过来,眼中有润泽余光,到跟前叫她,迟疑才应:“噢……学长,我还有点事,饭就不吃了,谢谢你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再沉默地绕进房去拿自己的背包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乌昭没跟进去,而是往她身后来的方向看,随后就有个身量极高的男生走出来,横跨着一道分叉,是直冲电梯去的,但刚好与这边休息间面对面时停了下,侧睨,狭长黯然的眼角视线压来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乌昭就在送走梁穗后与他措不及防打上照面,空气中迸滋出某种隐喻的暗含攻击性的锋锐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双方都没退让分毫,直冲冲的,僵持了有几秒,陈既白主动收起一抹不屑,继续步离-
nbsp;nbsp;nbsp;nbsp;那之后就彻底断联,梁穗下午去家教也没有碰见他,她做好他会不讲理的准备,但事实上,他差不多在表面履行了条件,没打过电话也没发过消息,更没有主动再找过她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一直到考试那天,他当真就没出现在她面前过。
nbsp;nbsp;nbsp;nbsp;按理说最安逸的也是那几天,梁穗什么都不用想,却也止不住烦乱,埋头只管复习时,用着他做的ppt,听取他所说的建议,好像没有再见过的人也变得无处不在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啃完她的笔记发现还有ppt这种好东西的柯冉立马凑过来求分享:“天呐你怎么还多做了一份这个?看起来更精细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柯冉太奇怪她有这精力了,但她也没劲多说,最后烦得直接关了。
nbsp;nbsp;nbsp;nbsp;那期间乌昭还在线上找她提过那顿失约的饭,也以备考为由推迟了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忙也不是假的,复习到半夜三更,每天两眼一睁就是看论文案例,背名词解释、构成要件……主观考试科目繁多,堆在一起闭卷,还只有法条能带进考场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也该谢谢陈既白的,他准备的东西都用了心,提到的侧重点没有废话,她能少了许多抓狂的时刻都多亏他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可他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讨厌,说喜欢她,却从没有好好地、纯粹地追过她。
nbsp;nbsp;nbsp;nbsp;考完试后,柯冉发消息说中午想出去吃饭庆祝,那时候梁穗还坐在自习室,回了个好,看了眼时间差不多,准备去跟她们汇合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从就近的后门出去,边低头整理背包中的书物,拉链带到一半时,蓦然听见前方几步距离的一道平调女声。
nbsp;nbsp;nbsp;nbsp;“梁穗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梁穗抬目看到谭怡,唇线抿直,耸起的肩一下平了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双方都没再靠近,走廊上人来人往,其实不适合交谈,但一想,她们本就没什么好谈的。
nbsp;nbsp;nbsp;nbsp;“有什么事?”
nbsp;nbsp;nbsp;nbsp;“没,这么大个学校可不容易碰到,不来问候一下?”谭怡冲她轻嗤,环着一叠书,从不落一副傲然姿态,“我搬出去,你过得还舒心么?”
nbsp;nbsp;nbsp;nbsp;梁穗现在对她没有好脸色,也没有好耐心,冷声:“是啊,托你的福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也没想到她那么答,谭怡反而笑了,“终于不拿出之前那清高做派了?我不是说过,你最好能一直祝福我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“现在也一样,”梁穗平静直视她,“我祝福你,所以你最好能把他拴住,别放出来祸害人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就差把“你心心念念不惜做三的那个,现在还对着前任穷追不舍”甩她脸上,羞辱,挑衅,可以衍化出各种阴暗含义。这完完全全击碎她所有引以为傲的资本,而说出这话的人甚至毫无想法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她已经自乱阵脚,咬紧着齿关,在梁穗即将走过她时,睁大瞳孔去瞪说:“你得意什么?你觉得我很可悲还是自己很厉害?梁穗,”她忽然笑起来,梁穗停住,侧目,听着她一句下言:“你才是最可悲的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莫名的感觉,对于这句话,梁穗长久的定在那,眼底有懵然迟缓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她想问,但没来得及问什么,电话响来,梁穗别开一眼,谭怡就径直走过她,进了自习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