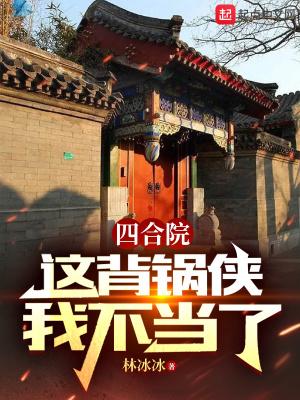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至死靡他 > 5060(第18页)
5060(第18页)
nbsp;nbsp;nbsp;nbsp;身体某处有灼烧痛感,他眼中情绪交加,却好像什么都不及看她重要。
nbsp;nbsp;nbsp;nbsp;“陈既白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平稳的声音被瞬间稀释卷进雨浪里,梁穗扔掉一张纸,又低头抽出一张,开始擦他的下颌,脖颈,伸出去就被透湿,雨,血,到后来其实还有泪,滚烫的,只是包裹在一起,分不清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她轻问他:“你不是很聪明吗?”
nbsp;nbsp;nbsp;nbsp;怎么会看不出来,这是算计呢。
nbsp;nbsp;nbsp;nbsp;陈既白闭起唇,血从嘴角溢,而问出这句以后,梁穗已经没有心思给他及时擦掉了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他们相视,僵持。
nbsp;nbsp;nbsp;nbsp;而后不远处传来另一道敲砸伞面的雨声,有条不紊的脚步接近。
nbsp;nbsp;nbsp;nbsp;梁穗的视角是背对,陈既白则稍微一侧就看得清徐步走来的苏虹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但只一眼就收回来,好似并不在意,重新放回到梁穗脸上,眼中对于真相的茫然,疑顿,不甘,通通消散在这张分明近在眼前,却又触不可及,分秒都在渴想的脸上。
nbsp;nbsp;nbsp;nbsp;“顾不上聪明。”他淡说。
nbsp;nbsp;nbsp;nbsp;迟迟才想起来为他抹去嘴角鲜血的动作悬顿住,纸巾贴在伤口,不动,梁穗缓缓抬起眼皮,一股莫名的热意烧得眼球鼓胀般得疼,喉口堵闷,发不出声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她看着他,感觉不到眼中的热流是否涌出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他也看着她,撑着最后一丝颓萎的神气看着她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又是这个眼神。
nbsp;nbsp;nbsp;nbsp;熟悉的,让人心境复杂的,才在包厢里就见过的一模一样的眼神,都在默声告诉她——
nbsp;nbsp;nbsp;nbsp;我知道,没关系。
nbsp;nbsp;nbsp;nbsp;骤闪的雷电光切裂灰天,大雨暴烈,地砖的泥缝被冲刷,溅起污浊水渍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她身上是湿冷,僵固,仿徨却麻木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为什么甘愿让她利用,甘愿被算计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为什么要做这些事。
nbsp;nbsp;nbsp;nbsp;要自毁。
nbsp;nbsp;nbsp;nbsp;要这么坏。
nbsp;nbsp;nbsp;nbsp;暴雨下视线,感知,思维,都被洗刷迷朦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但她清晰听见陈既白很低地接了声:“对不起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被她算计之后,对她抱歉。
nbsp;nbsp;nbsp;nbsp;没有问句,也不需要解释,现下也什么都不重要,像是深思熟虑,又根本没有空思考。
nbsp;nbsp;nbsp;nbsp;眼前的人虚虚实实,他只是喝了酒就见不到她,如果就此晕过去,她又会跑到什么他找不到的地方呢?
nbsp;nbsp;nbsp;nbsp;所以,他放弃了。
nbsp;nbsp;nbsp;nbsp;他对她说:“如果实在没办法喜欢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“如果欺骗是唯一能维系我们之间关系的介质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他尽量睁着眼,雨太大,总潲进瞳孔,脸色被溅得惨白,声息近乎轻弱,又努力一字一句让她听清地说:“一直骗下去,穗穗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高跟鞋的踩踏声停下了,密密层层的雨点填塞整条胡同,水露清洗砖瓦,淅淅飒飒。
nbsp;nbsp;nbsp;nbsp;时间仿佛在另一维度上静止,世界颠倒。
nbsp;nbsp;nbsp;nbsp;梁穗浑身冰冷,从他嘴角收回的指尖是僵的,敛头,尝试张嘴,想说话,呼吸却剧烈颤抖。
nbsp;nbsp;nbsp;nbsp;像是经过一场沉重而疲累的酝酿后,她看着他,眼底恢复波澜不惊的平,说:“没可能的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第二次说这句话,却更疏冷,更刺痛。
nbsp;nbsp;nbsp;nbsp;“陈既白,你为什么总能表现出一副好像很深情的样子?”
nbsp;nbsp;nbsp;nbsp;擦过他血水的纸巾揪紧在她手心,成一坨皱巴的硬体,她的心跳起伏不平,眼底却没有任何异样,“你给我绑设备,装定位,调查我,辞掉我的工作,强迫我,擅自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糟。”
nbsp;nbsp;nbsp;nbsp;呼吸落到这句的尾音,有了轻抖,她看向他的眼睛,也有了几丝深邃的悲伤,却字字咬牙:“你做的这些事,每一样,我都很害怕,很讨厌,非常讨厌。你还总是说喜欢我,我却只能讨厌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