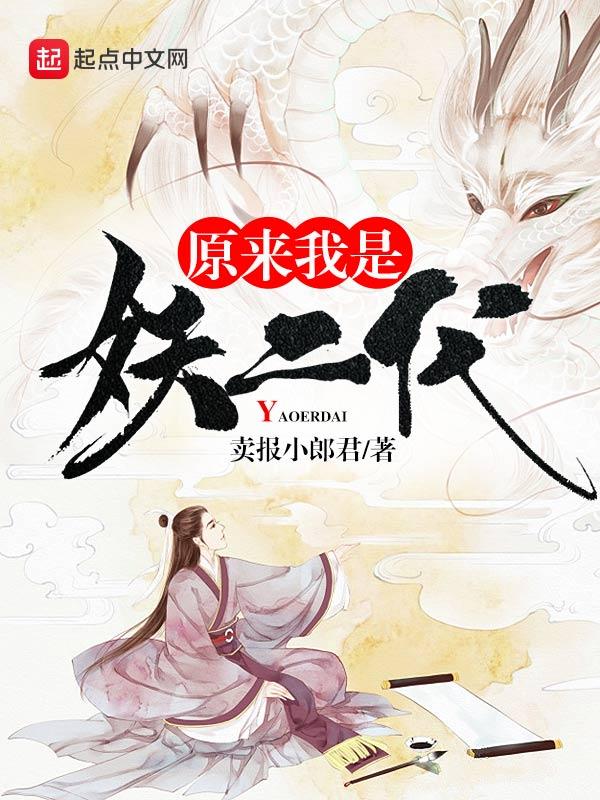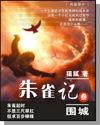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带着玩家在大唐搞基建的日子 > 210220(第28页)
210220(第28页)
他在心中暗暗警醒,按照吩咐去宣召几位宰相。
一进紫宸殿,看到皇帝兴致勃勃地站在墙边,正在仰头查看挂在墙上的大唐疆域图,几位宰相都是一愣。
等到李纯转过头来,叫他们过去跟他一起看地图时,几人更是忍不住恍惚了一下。
这一刻的李纯,像极了刚刚登基时的模样,意气风发、雄心勃勃。自从天兵出现之后,朝臣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种状态的皇帝了。
众人都有些唏嘘感慨。
但激动是没有的。
天下大势,如今已经很分明了,他们能做的事情也实在有限。
譬如今天这场议事,在几人看来,也只不过是走个过场,其实没什么好商量的。
雁来这个回鹘可汗已经是事实,连回鹘各部都已经被她摆平,大唐这边不过是补一个程序罢了。
答应,那雁来就仍是大唐的忠臣,回鹘则不仅名义上是大唐的属国,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被纳入朝廷的管辖范围之内,派遣官员管理。
不答应……这个选项根本都不会出现在他们脑海里。
即便上溯到贞观时期,对回纥六府七州采取的也是羁縻自治的策略,如果真的能做到深入治理,那就是能并肩甚至超越太宗的功绩。虽说功劳都是雁来的,但既然以朝廷的名义去做,那就还是大唐的。
至于雁来的势力扩张可能带来的影响,反正也不是第一次,也不差这一次。
所以他们真正要商量的,是怎么把这件事办得体面一些,在道义和法理上确定朝廷的主导地位,而又不会引起天兵的不满。
要两者兼得,实在并不容易。
但不管怎么说,皇帝能打起精神来,作为侍奉他的臣子,至少压力总会小一些。
虽然很快他们就意识到,自己想错了。皇帝并没有变成几年前的他,已经发生的事、已经造成的改变,是不会消失的,所以皇帝一开口,就又是那个阴晴莫测、让群臣难以招架的皇帝。
他指着地图上属于回鹘的那一大片地方,问道,“诸位先生以为,趁此机会在回鹘设置郡县,将之纳入我大唐治下,可行否?”
要不是还记得这是在什么地方,自己又是什么身份,几位宰相简直想回答他:这事你问错人了,我们说了也不算啊!
好家伙,他们还在发愁如何将朝廷那四处漏风的面子给糊一糊,让它勉强能看,皇帝却是连里子都想要。
这时几人才意识到,皇帝重新燃起斗志,恐怕并不是好事。
当下这个局势,他要斗谁?他能斗谁?
这段时间皇帝虽然阴阳怪气、情绪莫测,甚至在对待官员、勋戚和藩镇时更加雷厉风行,但在天兵的事情上,却有种认命了的摆烂,只要宰相们的提议过得去,他就全都照准。
现在怎么又回到了刚接触天兵的时候,跃跃欲试想跟对方碰一碰?
李吉甫心里最苦。
因为他从头到尾经历了李纯的种种变化,好不容易跟皇帝磨合好了,形成了一定的默契,一转眼李纯又倒退回去了。
虽然心里想骂人,但面上还是要绷住的。
不知道李纯发什么疯,但是他应付不了的场面,总有人能应付,李吉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甩锅,“郭常侍奏折中也提到想要进京述职,兹事体大,陛下不如召她入京,详细商议?”
有本事你去当着她的面提。
反正大战之后,主将入京述职,其实也是惯例了。
本来是为了嘉奖将领,拉近君臣之间的距离,后来逐渐变成了皇家防范武将坐大的手段——趁这个机会,或是调换去一个地方去任职,或是直接把人留在长安,自然就能切断他们跟旧部的关系。
安史之乱后,藩镇几乎不再入京朝觐,就是防着这个。
但雁来显然不是一般的藩镇,李纯敢宣召,她肯定就敢来。
果然,即便是此刻踌躇满志,觉得“我又行了”的李纯,也暂时不想面对雁来,于是连忙道,“征战辛苦,何况回鹘那边想来也有很多事务等着处理,离不得人。朕便想着,不如朝廷先商量出各大致的章程,再告知她。”
大概李纯自己也知道这个想法很不靠谱,商量出章程容易,要让雁来和天兵认可难,这件事想撇开她们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停顿片刻,他还是道,“安西军不是派了使者过来吗?就让使者代她觐见吧。”
几位宰相交换了一个视线,都觉得这样也不错。
总之皇帝有什么都冲着天兵去,别为难他们就对了。
只有李吉甫心下暗暗纳罕,皇帝那副斗志还真不是装出来的,而是真的有心想做点什么。
但这种想法他又不是没有过,甚至也实践过,然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,再多的计谋和手腕也发挥不出来。在接二连三受了打击、折了面子之后,李纯才选择了躺平摆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