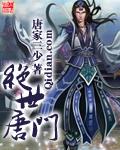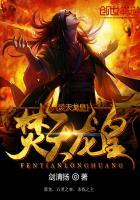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带着玩家在大唐搞基建的日子 > 260270(第16页)
260270(第16页)
众人连忙跟上。
至于刚才那个小插曲,自然不会有人不识趣地提起。
当然,不提起不代表不在意。
不管这是意外还是有人刻意安排,在李纯卧病在床,朝政操于雁来之手的情况下,它都像是一种暗示、一种试探。
只是越是在意,越是要故意忽视。
所以众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了悬挂在楼檐下的各色花灯上,然后不知不觉就投入了各种小游戏中,踌躇满志地想要攒齐兑换券,去换自己心仪的那一盏花灯。
……
雁来当然知道,大家都装傻,不代表这件事就不存在了,但是新年假期结束,恢复上班的第二天,就收到了一份劝进表,却还是有些出乎了她的预料。
……已经到这一步了吗?
“这人是谁?”看着奏折最右边那个陌生的落款,雁来问道。
李绛立刻答道,“此人原本是夏绥节度使的属官,去年考绩出众,便调回了京城,如今在清税司任职。”
藩镇改制时,也对当地的官员进行了考核,又因为有不少人未能通过考核,那些通过了的,便都临时暂代了各种重要事务,干得不错的后来都转正了,能被调动回京,那此人就不是不错,而是相当出色了。
被调到清税司,说明他擅长的是经济和钱财方面。
这种人才,在之前的大唐体系里很容易被忽视,但却能被玩家认可,也难怪可以回京了。
雁来合上折子,将它放在了一边。
李绛的视线跟着她的动作走,欲言又止。
这封奏折就是他递到雁来面前的——按理说,这样的奏折应该是密折,不该被雁来之外的人看见,但雁来一口气招十二个秘书,本就是为了给自己自己减负。
好在开工之前,雁来就召集众人开会,宣布了新的工作条例,比如对于接触到的奏折文书要保密、废除收润笔的陋习等等。
再说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
所以见李绛这样,她就笑道,“想说什么就说吧。”
李绛就问了,“殿下不做批复?”
他问的当然不是这个奏折,而是雁来的态度,因为批复之后,这本奏折就会被送到中书门下,里面的内容自然也就不再是秘密。
朝臣们要试探雁来的想法,但同样,雁来也需要试探朝臣们的想法。
雁来摇头,“一个投机者罢了。”
并不是说这样不好,在这个时代,像他这样不能靠科举出头的人,能够抓住机会并且做出成绩,并不容易。
只是这样的人往往过于灵活,而且赌性很重,所以这份奏折说明不了什么。
李绛听懂了。
而雁来给他的这个回答,某种程度上,也是一种表态——她不批复,只是因为这份奏折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朝臣的态度,所以她在等,等所有人的态度统一的那一天。
李绛在自己身后的架子上,腾出了一个单独的格子来存放这封奏折。
雁来下班是注意到了那个空出来的格子。
她并没有走过去看,但是看到上面只摆放着孤零零的一份奏折,她心里便隐隐有了猜测。
这段时间发生的事,让雁来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氛围。
有一种很多人伸手在后面推她的感觉。
不,这么说也不确切,那是一种更加柔和的感觉,非要说的话,有点像是在河里游泳的时候,水流从后面冲刷过来,无需耗费太多力气就能被推着前进。
但是现在的水流还不够大、不够快,所以也不够推着她抵达目的地。
幸好雁来的耐心很足。
……
尽管朝堂上下的注意力都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这件事情上,但雁来知晓时机未到,当然不会将精力浪费在这种事情上,干脆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。
她要做的事情,还有很多呢。
第一件,自然就是开启新活动,在吐蕃方面反应过来,让玩家用大唐的轻工业产品去占据吐蕃市场、拉拢吐蕃人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