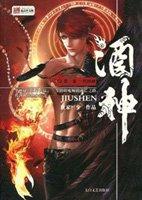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丞相大人是女郎 > 90100(第12页)
90100(第12页)
帐幔被猛的掀开,长风迫不及待地涌进去,知云愣在了门口。
“啊!姑爷,你流血”话语戛然而止,小言捂住嘴,怔怔地看着眼前对峙着的两人。
“不准进来,都出去。”赵参军已经进来的半个身子被用力推出去,他面色还懵懂着,知云已经一把拉住了门帘。
阳光和声音被隔绝在外面,窗口破开一个大洞的帐篷里,隔着一丈余的距离,萧存玉眼也不眨地看向谢铭。
“你竟然还活着。”语气听不出是失望还是嘲讽。
不久前。
尖锐的茶具碎片戳进皮肤里,她遵从刺客的指引走进帐篷深处,外面刘景周的说话声变得若隐若现。
仅有两人的空间中,她耐心和刺客周旋。
“兄台,凡事都好商量。”
“闭嘴。”刺客压低声音说,粗哑的年迈声音中有一丝莫名的熟悉,“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”
存玉肩上的伤口隐隐作痛,刺客的手紧紧钳进去,撕裂了还未完全愈合的伤口。
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征兆促使她低眼去看。
历经磨难的手闯入她眼里,枯瘦的五指,指缝里布满泥垢。
她眼珠一颤,看清了手背上横着一道狰狞的伤疤。
心脏钝痛,记忆翻涌,久远的哭声和争吵声重现。
血液开始沸腾,四肢百骸间充斥着的痛苦和仇恨重新占据她的身体。
“快点,还愣住做什么。”碎瓷片被鲜血染红,皮肉破开的疼痛竟也比不上瞬间在她胸腔炸开的绞心之痛。
“谢铭”
呢喃般念出这两个字,比云雾还轻盈,又比山石还沉重。
刺客的身形一僵,“你说什么——”
压抑不住厌恶,萧存玉用力推开他,谢铭向后撞在书桌上,书桌被撞歪,发出一声巨响。
什么人从门外进来了,耳边传来了嘈杂声,像隔了一层厚重的膜。
混乱间,谢铭的手打上她的头发,勾住金簪从肩上掉落。
“你竟然还活着。”
谢铭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人长发下的熟悉容颜,荒谬感裹挟着他,恨意随之浮现。
他颤抖着抬起手,咬牙切齿道:“逆女。”
萧存玉双眼像寒冷的潭水一样,潭水下是翻滚的岩浆。
“恶人竟没有天收,你还真是命大。”
谢铭被她的态度激怒,“你这是什么眼神,我是你爹,被流放你难道很开心吗?”
“当然。”
“贱种,老子养的你!”
“我没把你溺死是我心善。”谢铭唾她一口,“和你那疯子娘一样莫名其妙,不识好歹。”
面对自己的女儿时,他低微卑贱的身体突然高大起来,谢铭久违地找到了自己刚攀上知府时的意气风发。
他再低劣都是高尚的,再卑贱都是显达的。
他是绝对的权威和不容置疑的掌控者。
这个如花似玉的女人,他曾在她身上投注了无数心血。
她留着自己的血,轻贱她,卖她,吞噬她,敲髓吸骨,都是天经地义。
“你今年,有二十五了吧。”
萧存玉一言不发,捞起桌上刻着繁复花纹的匕首。
“啧啧啧。”谢铭吐出最恶毒的话,“你跟男人睡过没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