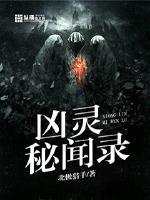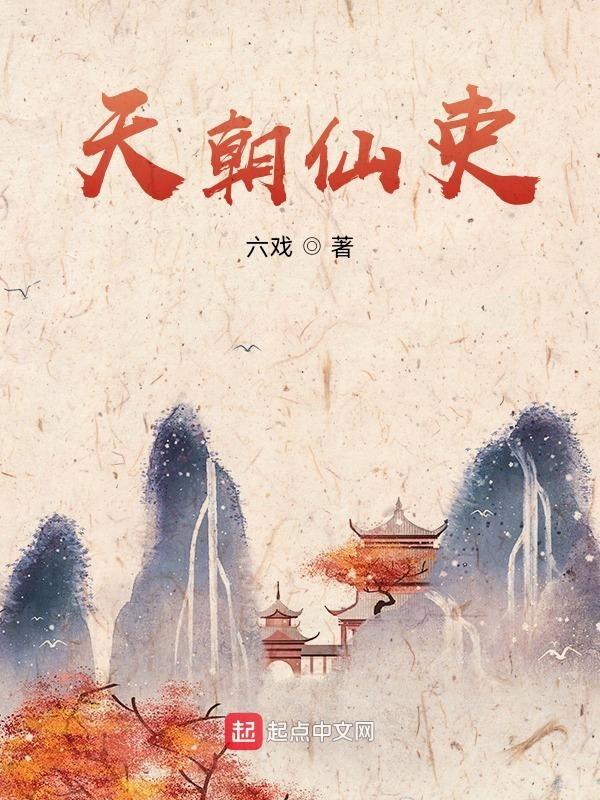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大秦:献图监国,始皇求我继承大统 > 140章 新花样(第1页)
140章 新花样(第1页)
咸咸阳城,在经历过一场疾风骤雨般的清洗后,诡异地安静下来。
朝堂之上,再无人敢公然提及科举的不是。
那些往日里眼高于顶的世家府邸,也纷纷闭门谢客,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与世无争的隐士。
监国府书房内,将闾看着张洪奎呈上来的密报,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“殿下,那些世家子弟,最近都‘勤奋’起来了。”张洪奎的声音听不出情绪,“往日斗鸡走狗之辈,如今也开始手不释卷,各家府邸都增聘了不少西席。”
“哦?”将闾放下竹简,“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?”
“不仅如此,”张洪奎继续道,“咸阳左近,忽然冒出不少‘善人’,匿名资助贫寒学子笔墨纸砚,鼓励他们参加科举。一时间,求学之风,竟似蔚然。”
将闾的手指在桌案上轻轻敲击着,眼神平静无波:“看来,他们是想出了新花样。”
这些世家,明面上不敢再闹,便转入地下,玩起了阴谋诡计。
突然冒出来的“勤奋子弟”和“匿名善人”,背后若没有鬼,他嬴将闾三个字倒过来写。
“查清楚那些‘善人’的底细,还有那些‘勤奋子弟’,看看他们究竟是真材实料,还是绣花枕头。”将闾吩咐,“另外,盯紧杜周和冯劫大人那边,任何想在考场规矩和钱粮用度上动手脚的人,都给本殿揪出来。”
“遵命。”张洪奎身影一闪,便消失在阴影中。
没过几日,治粟内史杜周便哭丧着脸找上了门。
“殿下,殿下啊!”杜周一进书房,便是一副天要塌下来的表情,“这……这各郡县报上来的应试名册,简直……简直堆积如山啊!有些偏远小县,连屠户的儿子、酒肆的伙计都报名了!说是……说是响应殿下号召,不问出身,人人皆可一试!”
他比划着:“臣粗略估算了一下,光是这初试所需的笔墨纸张,就得把国库的存货搬空一半!还有考场搭建、差役食宿……我的殿下,这银钱,它……它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!”
看着杜周那张几乎要挤出苦胆汁的脸,将闾反倒笑了:“杜卿,这难道不是好事吗?说明我大秦子民,求知上进之心,空前高涨嘛。”
“可……可是……”杜周还想说什么。
“钱粮之事,你不必担忧。”将闾摆了摆手,“国库若是不够,本殿自有办法。你只需将账目管好,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,莫让宵小钻了空子,便可。”
杜周见将闾如此笃定,心下稍安,但一想到那天文数字般的开销,依旧觉得肉疼不已。
紧随杜周之后,御史大夫冯劫也带着满面愁容前来。
“殿下,这应试之人骤增,远超预期,考场秩序、试卷评阅,皆是大难题。”冯劫忧心忡忡,“若是一个不慎,舞弊丛生,或是引发落榜学子不满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他并非反对科举,只是作为具体执行者,深感压力巨大。
“冯大人所虑极是。”将闾点头,“这正是那些人想看到的。他们想用人海战术,冲垮我们的考场,玷污科举的名声。但我们偏不能让他们如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