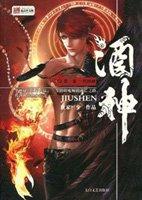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错撩权臣后他入戏了 > 离心(第3页)
离心(第3页)
“不用你们管,我生死自负。”狂风忽袭,吞没了她信誓旦旦的话语。
而谢徵玄从始至终没有起身,指节青白,扣住茶盏的手握得很紧。他的目光淬着寒芒,穿透朦胧的窗纱,追索着那抹绛紫,直至残霞中曳出一线流光,将最后的朦胧烟紫也绞碎在雾中。
案上冷茶倒映出他冷硬凛然的轮廓。
她后背的伤口甚至还未包扎,就那么着急要找到江颀风么,为此可以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?
不过几息之后,谢徵玄遽然掀袍,玄色大氅的貂毛镶边扫过门框,带起一阵细雪翩跹。
廊下的石砖结着薄冰,江月见的身子在彼端凝成一道模糊的影。
“回来。”
这声喝令震得雪都在颤,偏生那头的江月见跑得更快了,斗篷被风吹得猎猎翻飞,身形孤绝且倔强。
谢徵玄追到亭中枯梅树下时,江月见才哽着背影僵在那儿,枝头雪团簌簌落下,雪水顺着她的脖颈流进衣领。
“你胆子愈发大了。”
他伸手去拽她,大氅袖子却被枯枝勾住,金线错落缠绕枝头。
江月见趁机挣开半步,发间白梅发簪轻晃:“殿下是后悔用我了吗?”
他眉目冷冽,唇角微抿,牵起一抹自嘲的弧度。
“我不曾说过。”
江月见反问道:“行苦肉计之前,殿下虽有异议,但终究同意了此计。凭此,我成功让何慈和柳如是放下戒心,甚至让柳如是愿意以身犯险,送我进商队。殿下却上下嘴皮子一碰,便拒绝了他的邀约,难道不可笑么?”
谢徵玄收回手,缠绕的金线倏然崩裂。
他说:“你以为我为什么拒绝他?可笑?可笑的人难道不是我么?”
声音喑哑,叫她鼻头骤然一酸,酸涩的情愫自喉间慢慢溢出,惹得她心头躁动不安。
可她忽然又想起那夜荒山,风雪萧瑟,他说江颀风是叛国者,其罪当诛。
那抹酸涩更浓重了。
江月见垂眸,轻笑道:“殿下从始至终就明白,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尽早找到江颀风,为此我可以抛开一切。殿下若要阻我,那不如就此别过。”
话中决绝意味,比萧瑟北风还利,刮得谢徵玄瞳孔骤缩,指节青白。
昨夜此时,红烛帐暖,她洇红的耳垂犹在眼前,转瞬却能为了旁人与他撇清关系。
是了,她说过,她心系江颀风。
“好。”
谢徵玄冷笑着解开大氅,带着体温的貂毛兜头罩住眼前发抖的人,自怀间掏出一枚香薰硬塞进她怀里。
还不待她挣扎推拒,他已冷声道:“里面有粒蜡丸封装的药丸,燃之,香味七日不散。”
“我不要。”江月见倔强道。
“留着。一番相识,不过是为了给你收尸。”他冷硬开口,旋即转身。
梅树枝桠寒鸦掠过,抖落积雪,盖住两人纠缠的脚印。
江月见攥住那枚香薰,眼中雾气汹涌,终于还是放入了袖中,转身离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