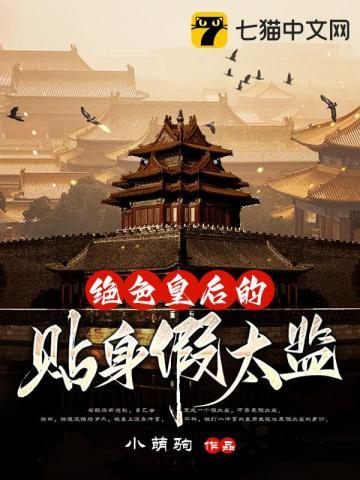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会长总觉得训练员在勾引她 > 第24章 番外某天店里来了位健忘的客人(第6页)
第24章 番外某天店里来了位健忘的客人(第6页)
“也不一定……”
“那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爱上别人。”
忘不掉?
付出一切?
呵,如果这就是爱的内容,那爱也太蠢了。
他夜舞已经记不得刚才被他俩共同服侍的马娘长什么样子,也不可能向其付出约定以外的服务。
那位马娘在上头时不要钱似的对前辈与自己反复念叨“我爱你”,听得他耳朵要起茧子了。
夜舞悲哀地看了看他可怜的前辈,听别的牛郎说,前辈是个不可思议的人,一个爱着所有马娘的人……牛郎店里的交谈总是如此夸张又肉麻。
但是就算这话被夸张了十倍百倍,前辈爱着的只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马娘,那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了。
更别提对这个不可思议的人来说,牛郎们对他的评价也存在没被夸大的可能性。
“你其实不用太把我说的话当回事。”前辈觉得自己说错了话,焦急地想要纠正。
“没关系的前辈,你说得对也好不对也罢。我想,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不掉谁,不会想为谁付出一切的。”夜舞翻身,侧躺着面向枕头另一端的前辈,自信地对那楚楚可怜的头牌笑道,“前辈,这样的我,算是没有爱的人了吗?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忘不掉,一丝一毫都忘不掉。
力道完全不下于殴打的挺腰,把脸抽疼的发束,被兽性填满的眼眸,这一切将五感彻底摧残,并随后嵌进了脑海,没有丝毫淡化的迹象。
哪怕当时失去意识了,但那些刻在身上的记忆总要把他拽回那一夜里,让他仿佛仍在被凌虐。
忘不掉大鸣大放漆黑的决胜服,忘不掉她额前那块冷漠的白纹,忘不掉她一黑一白一双长靴上露出的脚背,忘不掉那差点让他永远不能呼吸的手。
他痛苦地发现自己怎样也忘不掉大鸣大放。
那他的一切呢?他愿意全部献给大鸣大放吗?
是大鸣大放的话,就和他的意愿没关系了呀……
他在大鸣大放的面前只是个物品而已,哪有在使用物品的时候询问物品是否愿意被使用的道理呢?
大鸣大放在他身上宣泄能透过肉体使背后的床板塌陷的力量也好,从夜的开端持续索求到天明也好,哪怕是一切结束后连费用都不付也好……身为物品的他一切本来就是大鸣大放的,予取予求,哪还需要过问他自己的脆弱意愿呢?
于是他又绝望地认识到自己会为大鸣大放付出一切。
因为面前出现大鸣大放,瘫坐在草地上的他已经没法再正常思考。
在这种情况下,他便可以得出一个连他那不可思议的前辈都没法想出来的古怪结论——忘不掉大鸣大放,会为大鸣大放付出一切,也就是说,他爱大鸣大放?
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爱也太可怕了。
眼前的情况更是迫在眉睫,那个或许是他爱的马娘,可怕的大鸣大放,距离一度为负的女性,朝他靠近,直勾勾地盯着他,张嘴想要说些什么。
要问为什么牛郎会身着训练员制服出现在学校里吗?要威胁牛郎别把那晚的一切告诉任何人吗?还是说,要和牛郎约个时间地点吗?
他像当初在床上时一样,没法揣测对方的想法,无法预料她慢慢张开的嘴里会说出什么话,事实上,那晚在上了床之后她就没有一句话,她没必要和一个泄欲工具交流。
终于,带着好奇与疑惑,大鸣大放开口了,是个极简单的问句。
“你是谁?”
“咦?”
“你是谁?”好像是以为对方没听清,大鸣大放单纯而直率把极简单的问题重复了一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