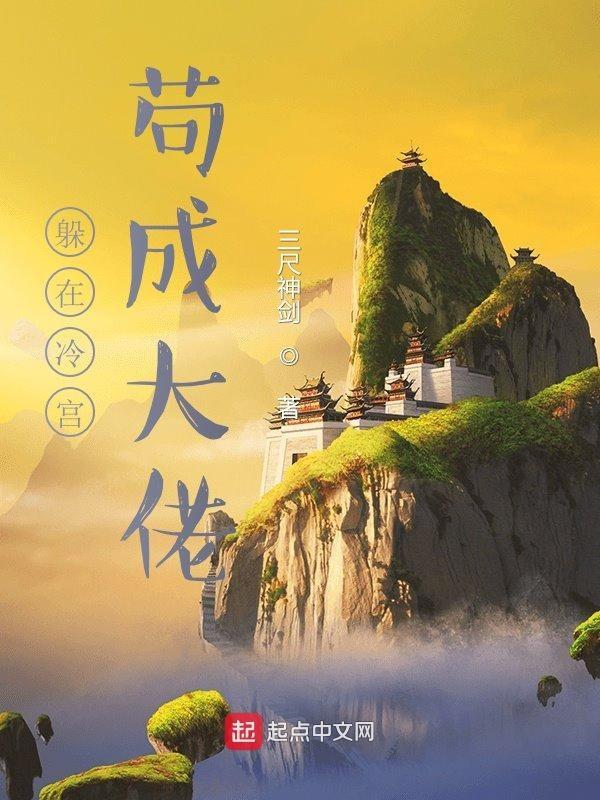书包书库>熟仙艳录 > 第19章 会亲戚母婿暧昧(第9页)
第19章 会亲戚母婿暧昧(第9页)
那少年哪里经过媚妇诱惑?
登时便觉口干舌燥,脸红笑道:
“以前的事都过去了,来日方长,哪有一堂之亲不见面的道理?”
那岳母闻言,意味深长道:“不,不是那种……不是……不……不对……不应该……”
赵曹氏心下慌乱,便猛饮一碗酒,那岳母虽早为人妇,却从未同男子有过花前月下的光景,不禁作少女态,熟花新开,倒比新花还艳,那熟妇正自娇羞,张洛倒觉奇怪,好似有股子劲儿,憋在二人身上,却止于画眉,看不清面目,糊涂间,那岳母倒喝开了怀,堵住张洛,你一碗我一碗地喝了起来。
那岳母举杯,女婿便亦饮,月不至中天,便见酒干。
那岳母喝得面若桃花,不住咯咯笑,饶是张洛酒量大,此时亦觉头晕目眩,中庭席散,人各回住处,张洛看时辰不早,便劝赵曹氏道:
“岳母在上,小婿已不能再饮,不如暂罢此厢,改日再饮吧。”
那岳母闻言,虽早已沉醉,美目惺忪,却仍不依道:“良宵难得……不行,再喝……我,我去拿酒……”
那醉妇扶着石桌挣扎起身,忽地腿脚一软,便一头攒在张洛怀里,张洛大惊,忙欲扶正那醉岳母,却见赵曹氏手阻足抵,一番挣扎下,索性赖在张洛身上,扭身挣体,就势坐在张洛腿上,复把张洛小半个身子埋进肉沟里,粉臂若藕,体香似麝,紧紧搂住张洛便不放手。
“岳母!岳母!你醉了!”
“没……我没醉……你不要走……”
张洛大惊,忙挣扎,可该是那少年命犯熟桃花,无论那梁氏温搂还是这岳母香怀,怎得也脱不开,倒叫那岳母紧紧搂住,口中喷出心头春桃花味的酒气,柔声轻语道:“洛儿……你给我的碧玉凤凰……不好用了……我的心里好热……那里也……”
“既是不好用了……那……”
那岳母还未待张洛说完,便“嘭”地捉住张洛的手,强引着向美人胯下探去,那少年哪里经过如此强暴的诱惑?
那手掌顺着赵曹氏平坦而紧实的小腹向下摸去,船行蓬蒿里,渐入佳境,便摸到一片比梁氏下面还茂盛的蓬草,水乡泽国,腾得赵曹氏身下一片潮热,游龙戏蚌,刚挨碰上软壳儿包着的蜜洞儿,便惊得忙抽出手,不觉沾上一片湿漉,及至细看时,便见满手的黏丝,晶莹剔透,丝里竟包着些珍珠般细小的泡泡,复闻一片香腻之气,柔柔弥散开来。
“看来我媳妇的香穴,原是在岳母身上长的,那淫水儿又黏,里头还泛着泡儿,确是体火过大所至。”张洛正自思忖,竟不由自主将那指尖琼胶放在口中吃了起来,便只闻一片香腻之气弥散,那岳母见俏女婿吃了淫水,遂惊喜过望,说话一发放浪起来:
“好儿子,吃那东西作甚?怪脏的。”
那少年遂尴尬笑道:“好……好教大人知,小婿自幼随师父学习医理,便知望闻问切,大人身体不豫,我这便是……”
那岳母不待张洛胡诌罢,遂笑道:“你这属馋猫的,遇见腥便要吃,还需找什么理由?分明便是馋了……不过好女婿,你妻娘的水儿……好吃不?不瞒你说,这世上吃过我的水儿的,也只有你梁姨还有你了……嘿嘿……你那干娘……是我闺中密友……”
赵曹氏酒劲正酣,迷糊间便不忌口了,便把甚言语,一发说了出来,那少年心中悚惧,便忙推岳母道:“岳母,您真醉了,我叫翠玉送您回去吧,您要是再这么拉扯,我俩便说不清楚了。”
那岳母闻言幽怨道:“不清楚有甚么不好?是妻是母,又有什么关系?我不比碧瑜儿差,只是年纪大了些,为什么不能有和她一样好的丈夫?你只见我刁,又怎知我受过什么?你丈人不碰我,已快一年了,前日又领回来个甚么性医,差点把命玩没了,饶是如此,他还要走,也不肯陪我……”
赵曹氏言罢,不禁扑在张洛身上,梨花带雨地哭了半晌,复低声粗喘道:“我……我只想要个男人来陪我……我……我需要你,洛儿……不知从何时,一遇见你,我里面就麻,就像着了魔一样……那碧玉凤凰……由是便不好使了……”
那岳母越说越动情,索性一口噙住张洛嘴唇,忘我地吻了起来,张洛大惊,挣扎之间,却被那岳母双手抱住脑袋,双腿蜘蛛般缠缚住身子,好似大虎吃小鹿,上嘴实啃,下嘴空咬,半是凶猛,半是柔情,又如蜘蛛猎飞蛾,缠住身子,便任她吃了。
“老天爷!吃人了!”
张洛心中大骇,恍惚间以为自己遇上了妖精吃人,半晌却不觉痛,只觉满嘴春桃酒气,夹杂美妇似麝体香,没挡儿地往鼻子里钻,便觉通体舒坦,恍若神飞天外一般。
“嗯……哼……洛儿……你个小骚货……勾了人家的女儿,还把……还把人家的心给偷了……小骚货,小淫贼……”
那美妇紧环住张洛身子,一双美手好似生出牙一般,不住在少年身上摸索噬咬,那少年本也挣扎得紧,却不知那岳母使得甚么法门,一条粉舌撬开牙关,用力往张洛舌头上一刺,那少年登时便觉周身雷打般酥麻,浑身上下,只有一处不是软的,便挺在当场,任那淫法高强的妇人吃去。
“翠玉!翠玉!救我的命来!快把岳母拉开!”
张洛大惊呼喊,却见赵曹氏淫笑道:“这是我的居处,认你叫破喉咙,也断不会有人理你,小淫娃,你今日认了命吧……”
那岳母遂把夸紧贴在张洛大腿上,一边啃馒头似的吃那少年的软嘴,一边卖力地坐在张洛大腿上扭腰挺胯,但见那少年只觉自己好似落进了柔情织的大网,美肉造的地狱,纵使手脚一并挣扎,亦寻不见着力处,又好似掉在油缸里,纵使快淹到头顶,却端的舒坦柔滑,直教人难舍难离,恨不得找个眼儿,狠狠地钻进去,方才泄得出邪火去。
那熟妇骚情,勾得那少年亦起了火,正欲越礼,大行强暴时,却见那岳母身子猛地颤了起来,纵使口中叼着张洛的舌头,亦不禁呜呜地叫唤,好似有甚么筋强骨壮的兽物在身子里来回乱窜,过了半晌,方才见那醉妇松弛了身子,猛地软在张洛身上,复觉大腿上一片软腻柔滑,好似有人在上头打破了蜜罐子,黏浆甜汁,忽地澎湃汹涌而来。
熟潮易来,半晌泄罢,那少年方才怔怔回过神,但见那岳母双睫轻交,美目失神,喷兰吐麝,热气氤氲,倒没了方才那生猛的劲头儿,却像个吃饱的狸奴般慵懒睡去,只是嘴里还紧含着少年的舌头。
张洛说不了话,便推摇了那醉妇几下,却见赵曹氏竟闭上眼,轻声打起呼噜来,张洛无奈至极,欲火窜了上来,本欲不顾那妇人睡着,就地正法了她,心下却尚存理智,大婚头一日奸了睡着的岳母,确实不太地道,遂狠狠掐了掐腿内,疼息了邪火,方才顾抽出舌头,呼唤翠玉至切近送那醉眠的岳母回房休息,安顿罢,便听那大丫鬟道:
“好个姑爷,亲岳母亲得脸都花了。”
那翠玉心下酸意暗涌,言语间不禁阴阳起来,张洛见翠玉吃醋,遂赔笑道:“好妹妹,今日之事,不是我用的强。”
那丫鬟便道:“你休说花言巧语与我,谁上了谁,你自己心里清楚。”
那少年闻言,遂沉吟半晌,复笑道:“你是通房丫鬟,也是岳母娘子都信得过的人,好翠玉,好妹妹,你是个通情理的人,你若生了气,我真不知该怎么哄你了。
翠玉闻言笑道:“好一张坏嘴,只要是个女人,都能让你给哄了,夫人前般那样嫌你,今日还能和你亲到一块儿去,你本事大呀……唉……你个坏蛋,我原本确实想生你气来着,可念在明日……你知道该怎么做的。”
那丫鬟哼一声娇嗔,一跺脚走了,张洛忙了一天,也自去将息,转过天来,便是大婚之日,那少年一路奔走忙碌,终得岳母青眼,亦要与佳人成全佳偶,却不知大婚之日,洞房之际,又待怎得理会?